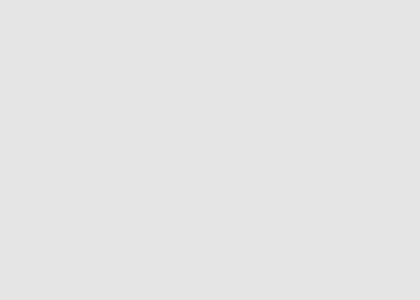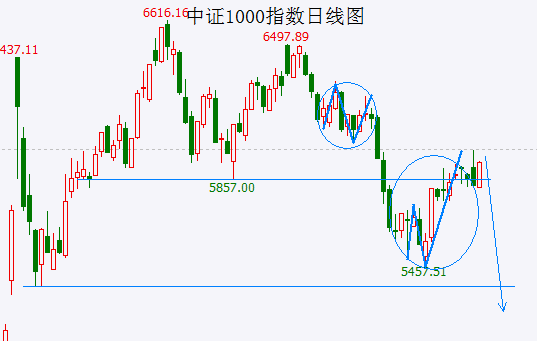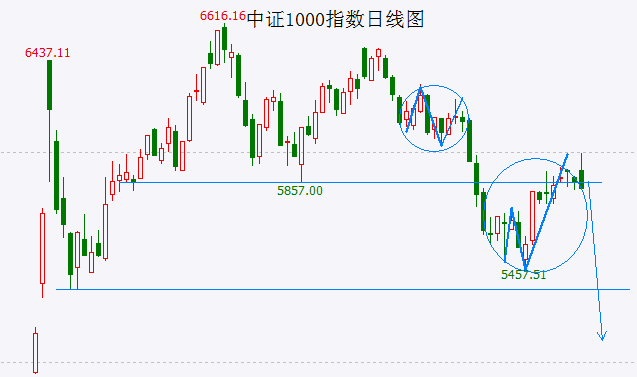日本強排20天后:一年投入成本超百萬,有漁民為生計發愁,鰻魚價格下跌超60%
9月8日下午3點,日頭正曬,碼頭上的海腥味撲鼻而來,對甄麗來說,這是收獲的味道。她早早來到碼頭等待自家的漁船,這是開海后的第二次回港。
每年9月1日開海,是甄麗最期待的日子。但此次,她卻多了一層隱憂,“發愁啊,核污水對我們肯定會有影響的。”
但具體影響多大,甄麗也說不清。
當地時間9月11日正午,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污染水首輪排海作業結束,總計向太平洋排出7788噸核污水。半個多月前,8月24日,日本正式將核污染水排入海洋,并計劃排放30年。
無疑,首當其沖被影響的是“靠海吃飯”的人。
根據農業農村部發布的數據,2022年中國漁業經濟總產值為30873.14億元,其中海水養殖產值4638.84億元,中國海洋捕撈產值2488.91億元,從事海洋捕撈的漁民超過100萬人。
“漁家艱辛多忌諱”,從登船習俗到口頭避讖,向海取索、靠海生活的人們總是小心翼翼,面對浩瀚的海洋,他們謹慎、敬畏。而核污水,則給變化莫測的海洋又蒙上一層陰影,有人為此發愁,有人則試圖忘記。
“既有遠愁也有近憂”
9月1日,北緯35度以北的黃渤海海域結束了為期4個月的伏季休漁期,漁船紛紛出海捕魚。在山東膠東半島,沿著海岸線,分布著大大小小的漁港,威海的乳山口港就是其中之一。
這里的捕撈漁船主要以近海捕撈為主,早的當晚就可回港,遠的則要三四天,乃至一個星期,主要漁獲包括鲅魚、帶魚、黃花魚、對蝦、爬蝦、螃蟹、海螺等。
漁船回港的時間不定,倉滿則歸,因此,無論一天中什么時候前往碼頭,總能看到歸港忙碌的漁民。
9月8日,下午3點左右,甄麗家的漁船靠岸。漁船三、四天回港一次,這是開海后的第二次,船長是甄麗的丈夫,另外還有五名船員,船艙里是被冰鎮著的海蝦和皮條魚,滿滿當當。
船靠岸后,傳送帶的發動機轟鳴著,一箱一箱的魚蝦,被運送上岸。船員再將魚蝦盡數傾倒在碼頭上的大桌上,交由村民們將魚、蝦分揀開。
這樣簡單又耗時的工作,養活著100多位村民,他們多為60歲以上的老年人,“三四天來干一次,一次四五個小時,一個小時能賺12元。”
甄麗家的船不算大,是一艘玻璃鋼船,不捕撈大魚,以蝦為主。“男出海、女織網”是當地漁民的一種傳統模式,也被稱為“夫妻船”。丈夫負責出海,甄麗則操持岸上的理貨、售賣、理賬、人員調度、修補漁網等事務。
一家人的生計,押注在一艘船上,像甄麗一樣的漁民家庭,齊心卻脆弱,容不得任何的意外。
面對無法控制的核污水,甄麗既有遠愁也有近憂。
她擔心,到了明年,核污水真的會影響到海里魚蝦的生長,進而影響到漁獲產量,更擔心,沒人敢吃海鮮,“撈回來了賣不出去怎么辦?”
除了無法預料的明年,更直接的是,今年的漁獲價格已經受到了影響。除了海蝦,甄麗家的漁船還會捕撈少量海鰻魚,主要出口日本。收魚的魚販告訴她,鰻魚的出口需求下降,因此價格也只能降低。
“以前海鰻魚能賣15、16元一斤,好的時候能賣20元,而現在魚販只用四五元一斤的價格收魚。”差距天壤之別,甄麗嘆氣。
“成本那么高,拉的貨又不值錢,有什么意思?”甄麗聲音帶著笑意,眼眶卻有些泛紅。她算了一筆賬,“之前用的是更小的木船,這艘船是8年前貸款100萬買的,這幾年才剛還完;今年出海前,光維修保養又花了十幾萬;五個船員,一個船員的工資一個月18000元,分揀魚蝦的零工每次就要6000元,還有船上燒的油、設備的錢,都是花銷。”
作為船長,甄麗的丈夫則來不及發愁,他只想在變故出現之前多出海,多收獲。開海后,他連回家休息的時間都沒有,船三四天才靠岸一次,僅停靠兩三小時,卸貨、整理漁網、加油、補充生活補給,便又匆匆離港。只有出現風浪無法出海時,才不得不給自己放假。
和甄麗家“夫妻船”的模式不同,孫彤家的生意做得更大,6年前起,她和丈夫陸續購買了6艘大鐵船,和一艘更小的收獲船,總共7艘船,以捕撈鲅魚為主。
捕魚體量更大,需要雙船同時作業,6艘船兩兩配合,常年在海上運轉,除了風浪從不歸港,收獲船則成為中轉站,載著漁獲一天歸港一次。
扣除各項成本,一艘船一年能創造20萬元左右的價值。但成本也是巨大的,船員、船長是雇來的,每艘船上有6至7人,僅從9月到過年這5個月,一位船長的薪資是20萬,船員則十余萬元。今年出海前,維修6條船又花了50多萬。
開海后,孫彤每天凌晨5點起床,前往碼頭等候收獲船歸來,和她一起等待的是批發商的一輛輛空卡車。9月9日一早,船一靠岸,孫彤就開始連軸轉,來找她買魚的批發商并未減少,“和往年沒什么差別。”
鲅魚是常見的家常食材,山東人的餐桌上,離不開鲅魚餃子,在孫彤看來,這或許是她們受影響較小的原因,“核污水暫時對我們還沒什么影響。”孫彤的回答十分簡短,她的精力都集中在手中的賬本以及和魚販的交涉上,無暇顧及其他,“不想擔心那么多,先把每天的事忙好。”
不過,孫彤也懼怕海上的不確定。“能不能上船看看?”“不要上船!女人不能上船,我都沒有上去過。”女人不上船、不出海是當地的習俗,孫彤也說不清原因,但為了規避海上的任何風險,她寧愿遵從。
買海鮮的人少了三分之二
同樣的憂慮也在這條產業鏈的下游蔓延。
9月9日下午四點,三三兩兩的顧客偶爾經過陳薈的攤位,陳薈立馬招攬生意,“買蝦嗎,100塊三斤。”這里是乳山最大的海鮮市場,上百個攤主們和陳薈一樣,正在翹首期盼顧客的到來。
“現在能看到三三兩兩的人都算不錯了,前幾天好多時候連人都看不到,和之前差老大老大了。”陳薈說,往年9月1日開海之后是乳山當地的海鮮旺季,不管是本地人還是游客,都趕來嘗這“第一鮮”,“今年的人比之前起碼少了三分之二,核污水排放之后,好多人都不敢買海鮮了,比前兩年疫情的時候人還少。”
陳薈的攤位,主要賣蝦、螃蟹、海腸,從20歲就開始從事水產生意的她,現在已經35歲,她坦言,“這是15年來生意最難做的一年。”
“一般是清晨進貨,之前好賣的時候,中午或者下午一兩點就賣光可以收攤了。”而當天下午4點,陳薈的攤位上還有不少鮮活的大蝦在水中暢游,“這樣下去的話,對我們沖擊很大。”
比起陳薈,汪姨的攤位更靠內部,經過的顧客就更少了,她坐在椅子上,看著自己滿攤的海魚發呆。8月24日排海當天下午,汪姨和攤主們都格外關注,守著直播,互相傾訴著,“大家都特別擔心,又憤怒又難過。”
汪姨年近60,在這個市場賣魚也有近20年了。每年,她最期盼的也是開海之后的這幾個月,“開海之后人流量大了,魚的品種也多了,接下來又是過國慶節、過年,是一年中生意最好的時候。”沒開海時,在5月到9月的四個月休漁期內,汪姨只賣一些養殖水產,但生意一般,只能基本維持著一年兩萬六的攤位費。市場里的更多攤販,在休漁期若不賣養殖水產,則會給自己放假。
前20年,汪姨的丈夫負責進貨,她則守攤,日子平淡地過著,她算不清每年具體賺了多少錢,只覺得2019年之前行情最好,自從疫情之后,生意就逐漸變淡了。而今年的生意,則更淡,“進貨都只進了一半,怕賣不完”。
算不清具體盈利的汪姨,現在對一個數字格外敏感,240。
核污水排海后,根據清華大學的模型,污染物到達中國海域的時間,“240天之后,萬一污染真的過來了,真的不知道怎么辦了。”
“哎呀,再吃幾天,咱就不敢吃(海鮮)咯”,前些天,一位老太太從汪姨的攤位前路過,嘴里的自言自語被汪姨捕捉到,印證了她的擔憂,“很無奈,她說的是實話,但是我聽著很難受。”
“咱們這里就是靠海吃海”,汪姨說,威海乳山還是山東有名的旅游城市,當地的海景房房價也極低,幾萬元就能買一套,催生了不少旅游、購房、康養的需求,“等到污染了,誰還來海邊玩?誰還來海邊買房?”
徐娜算是市場里的“新人”,3年前辭職創業,開了水產鋪子,主營各類海魚和蝦,在她看來,今年開海后的確比往年人少了,但不一定是因為核污水。
“前兩個月正值暑假,來威海玩的游客特別多,大家都說‘進淄趕烤,進威趕海’,開海后正好趕上了假期結束,游客走了。”同時,開海之后,賣海鮮的競爭也大了,顧客進一步被分流,“超市、小市場、攤販、微商團購都開始賣海鮮,還有顧客直接到碼頭去買”,徐娜說。
此外,今年開海后的客流比前幾年開海后的同期少,徐娜則認為是因為前幾年正值疫情,“疫情時好多小市場都沒開,顧客都來我們這個大市場買。”
作為游客的邱銘,和徐娜的感受一樣。
9月10日,她前往青島游玩,“本來是抱著最后一次來海邊的心態來玩的,但來了之后發現很多人都沒有談論這件事,海邊的景點、海鮮大排檔還是有不少人,或許大家真的在慢慢淡忘吧。”
在徐娜看來,隨著時間推移,大家對核污水的隱憂逐漸被忙碌的日常覆蓋。
“一開始市場里好多人都很擔心,還有人想轉行,但現在好像這個事就這樣過去了。”至于轉行,徐娜說,“還是走一步看一步吧,我也不能說停就停了。”
(文中采訪對象均為化名)
(來源金融界)大眾商報(大眾商業報告)所刊載信息,來源于網絡,并不代表本站觀點。本文所涉及的信息、數據和分析均來自公開渠道,如有任何不實之處、涉及版權問題,請聯系我們及時處理。大眾商報非新聞媒體,不提供任何互聯網新聞相關服務。本文僅供讀者參考,任何人不得將本文用于非法用途,由此產生的法律后果由使用者自負。
如因文章侵權、圖片版權和其它問題請郵件聯系,我們會及時處理:tousu_ts@sina.com。
舉報郵箱: Jubao@dzmg.cn 投稿郵箱:Tougao@dzmg.cn
未經授權禁止建立鏡像,違者將依去追究法律責任
大眾商報(大眾商業報告)并非新聞媒體,不提供任何新聞采編等相關服務
Copyright ©2012-2023 dzmg.cn.All Rights Reserved
湘ICP備2023001087號-2